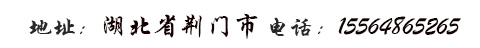晚明关中奇士王徵
|
王徵(—),字良甫,号葵心,中年皈依天主教后取圣名斐理伯(Philippe),明末陕西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温丰乡(今泾阳县属咸阳市)人。王徵出身农家,祖父王云“悉力农亩,寿八十有七”,一生清贫自守,行善积德,人称“老善人”。父亲王应选(字浒北)在家乡私塾任教,是一位勤学笃行的乡村知识分子。平日里他手不释卷,于经史诸子无所不览,看到书中忠孝大节昭著动人者,便动手抄录并反复记诵。后来,他还把圣贤故事编成歌诀(即《浒北山翁训子歌》),用以教导子女。此外,他还精于算术、地理、星命,著有《算术歌款》一卷。父亲的言传身教对王徵一生影响甚大,直到晚年,他“回忆严诲,时切注然,偶睹遗音,恍聆警狄”,意思是说老来忆及父亲,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,恭读父亲遗留的著作,仿佛又回到了幼时聆听父亲训诲的场景。母亲张氏出身文墨之家,慈惠勤俭,她生子二人,王徵是其长子。据史书记载,王徵“生而颖异岐嶷”,意思是他天生聪慧过人,且有不少奇思妙想。因此,父母对他期望甚殷,希望他将来能考中进士,光宗耀祖。 王徵小时体弱多病,每次发病,一连几天啼哭不停,情况十分危险。母亲焦虑万分,日夜呵护,不断地请医问巫,求神祷告。当时家贫窘迫,母亲就用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首饰换钱贴补,王徵后来回忆说:“徵之有今日,皆从先慈苦辛中全活之也。” 七岁时,父母让王徵跟从舅舅张鉴学习经史。张鉴,字孔昭,号湛川,人称湛川先生,是当时誉满关中的理学大儒。他博学广识,为官清正廉洁,深得百姓爱戴。在舅舅的悉心教导下,本就好学多思的王徵更加勤奋刻苦,他不但“能日诵百千言”,有时还自己出题做文章,一时被亲友传为佳话。除了精通理学,舅舅张鉴还善制各色战车及易弩、火弩等兵器,皆巧思独运,人见之则惊叹不已。这些奇器制作激发了王徵潜在的探求机械原理的浓厚兴趣,从此他迷上了奇器之学,而且一发而不可收,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癖好。王徵后来能奋力西学,成为与徐光启并称的一代科学家,皆得益于舅舅对他的科学启蒙。 由于长时间跟随舅舅学习,潜移默化中,王徵不但学问日益深广,写得一手好文章,而且胸怀坦荡,慨然有经世之志。他对舅舅深怀虔敬,一直尊称为“舅师”,至死不改。 万历十四年(),王徵考中秀才,进入当地县学学习,他仰慕北宋范仲淹的为人,便以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语作为座右铭。 万历二十年()秋,24岁的王徵进城参加乡试,考中举人,乡人皆来道贺庆祝,但不幸随之而来,不久母亲便病倒了。王徵和妻子多方延医调治,却收效甚微,王徵遂于风雪中“短袄布靱,十步一拜,泣祷于六十里外孙真人(孙思邈)之洞”,其孝行感人心怀。但母亲的病情仍丝毫没有起色,卧床数月后,母亲终于次年二月辞世。弥留之际,母亲无比遗憾地对王徵说:“我辛苦半生,只盼望能看到你考中进士,为我披上霞帔(朝廷恩赐的命妇的礼服)的那一天,现在看来是等不到了……”母亲的一生期望最终化作泡影,王徵心如刀绞,他暗下决心,一定要实现母亲的未竟心愿,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,迎接他的却是近三十个春秋的科考厄运。 沉迷奇器 万历二十三年()春,25岁的王徵进京参加会试,结果不幸落第。但他矢志不渝,此后他屡考屡败,屡败屡考,终于在第十次会试时考中进士,得偿母愿,而此时他已经52岁了。 从中举到登进士第,在这长达28年的时间里,除了科举考试,其实王徵一直都在忙碌着。自从少时舅师张鉴开启了他的科学志趣,他的创造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被激发出来。他曾对古时的璇巩玉衡(观测天象的仪器)、木牛流马、连弩等巧夺天工的发明非常神往,并为这些奇巧制作的失传而痛惜不已,他期想模仿古人而把这些东西重新创制出来。他苦苦探索这些奇异机械的奥妙,长年累月,“眠思坐想,一似痴人”,深陷其中而不能自已。这些机械制器在当时皆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,为君子所鄙,因此王徵经常受到乡邻亲友的嗟怨讥刺,但他性情宽和,并不以此为意。不仅如此,他还经常去拜访乡间的能工巧匠,并与之进行切磋交流,如合阳布衣马了贪,此人能创制兵轮、战车数种,是与王徵交谊最深的同行知友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多年的摸索试验,王徵终于成功制作出了木偶机器人、自行车、代耕(耕作工具)、轮壶(自鸣钟)、虹吸、鹤饮(引水灌溉用具)、风硝、自转磨、活动木以及连弩、自飞炮器等几十种半自动半机械化的奇器,这些机械器具中有不少是王徵自己的发明创造。据说,每年春夏耕作之时,王徵便会驱使自制的木偶下田从事舂壳、箕米、汲水、烧饭、揉饼、拉风箱等繁杂劳动,木偶“机关转握,宛然如生”。到收获时,他则用自行车载运禾束,往来道路田间。乡人看后大为惊羡,以为诸葛孔明复岀,于是纷纷效法仿制,一时传为美谈。后来王徵还将这些制器及研究所得整理成书,写成《新制诸器图说》,并刊行于世。 由于王徵长年沉溺于奇器创制之中,从而荒怠了正经学业,科考中他屡试不第,恐与此有极大关系。或许他内心对举业并无兴趣,只是自幼所诵习的儒家修身济世的信念深印心中,而母亲临终前的殷切期望又时时萦绕心头,所以每到大比之年(每隔三年一次),他便进京赴试。每次进京他都会逗留数月,当时京城云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,如利玛窦、庞迪我、龙华民等,一些有识之士皆与之结交,西方的制器之学和天主教教义便在这时开始传入中国。西学对王徵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,他不仅对西式制器向往不已,而且在精神上也渴望找到依托。自从母亲去世后,他开始思索关于生死的大命题,于是从诗书转向“道书”,希望能在道家思想中觅得精神依傍,因此中年后他便自称“了一道人”,但寻觅多年却茫然不可得。 万历四十三年(),友人赠与王徵《七克》一书,45岁的王徵读了这部宣讲天主教教义的书后,“见其种种会心,且语语刺骨,私喜跃曰: 是所由不愧不作之准绳乎哉!’”多年的精神飘荡终于有了归宿。第二年,他便借进京赶考的机会见到了《七克》一书的作者庞迪我,两人相谈甚欢。不久,在庞迪我的解说引领下,他受洗并皈依于天主教,直至终老,在此之前,“天主教三柱石”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皆先后受洗,成为中国第一代儒士基督徒。 步入仕途 天启二年(),王徵考中进士,当年六月他就被任命为广平府推官(掌管司法刑狱的七品官,府治在河北省永年县)。到任不久,保定巡抚张凤翔听说他熟谙兵事,即召他赴恒阳协助练兵。他依照舅师先前所授的诸葛武侯八阵合变图法,教士兵严格操练,同时整备军械,严明军纪,一时士气大振,张巡抚惊叹为“诸葛再生”。当时广平辖区内连年发生水灾,民众苦不堪言,王徵釆取大禹“疏而导之”的治水方法,开河筑堤,不仅消除了水患,而且灌溉田亩数千顷,百姓无不欢呼称庆。 天启四年()春,王徵因继母去世回乡奔丧守制。丁忧(指古时官员离职居家为父母守丧)期间,他悉心研究和体察天主教的教义,对天主的信仰更加笃诚。当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正在山西传教,王徵得知后便热情邀他来陕开教。金尼阁博学多闻,精通华语,两人相见甚为投合。抵陕后,王徵请他住在自己家里,并为家人宣讲授洗。金尼阁通晓中西字学,王徵便跟他学习拉丁文。金尼阁还将刚写就的《西儒耳目资》(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)一书的初稿拿给王徵参详,王徵看后大加赞赏,认为这是学习中国古音韵学的捷径,两人于是“相互质证,细加评核”,历时半年才告竣。《西儒耳目资》是“欧洲音韵学输入中国最早的一本书”(刘半农语),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贡献卓著,王徵也成为中国最早学习拉丁文的学者之一,是尝试汉语拼音的先驱。 天启六年()冬,王徵服丧期满,于是进京等候补授新职。当时传教士邓玉函、龙华民、汤若望三人正在北京奉旨修订中国历法,一向热心好学的王徵一进京便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他们。原来他在广平当推官时,曾读过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撰的《职方外纪》一书,里面所载录的诸多西式奇器(有文无图)让他大开眼界,对此他一直神往不已,盼望能有机会一睹为快。邓玉函、龙华民、汤若望将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千百种制器图一一拿给王徵观看,并详加指点,王徵喜不自胜,日夕沉浸于其中,种种奇制必细究其妙用,很快他就将全部图籍览阅完毕。在邓玉函的指导下,他又将那些最关乎国计民生、最简便、最精妙的器械内容编译为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一书,以期有裨于世人。在翻译过程中,王徵还创译了许多新的术语,如重心、杠杆,流体、齿轮等,皆为后人所广泛使用。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开风气之先,是我国历史上首部介绍西方机械知识的著作。 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完稿后,王徵便赴扬州再任推官。时太监魏忠贤权势正炽,全国各地皆为他建立生祠,淮扬巡盐御史许其孝为表忠心,也在扬州为他建了一所“瞻恩祠”,各级官员纷纷前往拜谒,唯独王徵与淮海道兵备副使来复(陕西三原人)拒不往拜,时人称为“关西二劲”。作为一个不附权贵的“劲士”,王徵却有一副“畏天爱人”的情怀,他体恤民众,时时以百姓为念,他曾手书一副对联以自警:“头上青天,在在明威真可畏;眼前赤子,人人痛痒总关心。” 崇祯元年()九月,王徵的父亲去世,为官近一年半的他不得不回乡丁忧。而此时明王朝大厦将倾,人民怨声载道,适值陕西灾荒严重,庄稼颗粒无收,饥民纷纷揭竿而起,“闯王”高迎祥常率军在关中一带烧杀抢掠,乡民人心惶惶,惊恐不已。王徵遂与当地乡绅商议建立乡兵,以自救自保。在他的倡议下,三原、泾阳两县乡民自发组织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地方武装“忠统营”,使流寇不敢随意进犯,时高迎祥军“往来飙忽数千里,秦无完城,独泾阳、三原安堵”,乡人的生命财产俱赖此得以保全。 服丧期满后,王徵经登莱巡抚孙元化推荐,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辽海监军(正五品官),协助孙元化把守清兵渡海进攻的防线。未料上任不足半年,军中参将耿仲明、孔有德因粮饷不足领兵在吴桥(山东、河北交界处)倒戈造反,史称“吴桥兵变”。孙元化、王徵等一干人员皆受牵连入狱,后来孙元化被斩杀,王徵被判“戍近卫“,不久便遇赦还乡。 年老归里 崇祯五年(),62岁的王徵回到泾阳老家,从此不再出仕。不久,他便在终南山下购地修筑了一座精巧的别墅,名曰“简而文”,意思是费不多而景致颇饶,地虽小而眼界却宽,作为晚年隐居著述的幽清之所。在这里,王徵写下了《两理略》(从政实录)、《崇一堂日记随笔》(与汤若望在西安崇一堂的交谈记录)、《草野杞谈》、《吁泰衷言》(时事著作)、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》(机械工程学著作)等著作,他自述这一时期的心情:“见之者每笑白发衰弱,复作青春学子,岂其老苦未尽,抑亦书债难还?然而我顾乐此不疲也。”与圣人孔子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的书斋情趣颇为相合。 虽然王徵在书斋中与知友谈诗论文、著书自乐,但他并未忘怀时事,他天生一幅济世热肠,特别是皈依天主教后更深以救世济贫为念。崇祯七年(),陕西又发旱灾,赤地千里,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“大饥”现象。王徵心系乡民,他以天主教的名义在家乡创办了慈善团体“仁会”。仁会以食饥、饮渴、衣裸、顾病、舍旅、赎虏、葬死七事为救济要务,结果在这次大旱中“全活千百人”。为广播天主的福泽,王徵还在鲁桥镇的一处住宅内设立了一所天主教堂“崇一堂”,作为公共祈福的场所。 崇祯十六年(),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西安,次年李自成在西安称王,建立了大顺政权。为笼络人心,李自成派人四处罗致地方名士。时王徵年岁已高,然声望素著,李自成多次遣人至其家劝说礼聘,但王徵不为所动,他立誓忠于大明王朝,并以死抗争。为此他还提前为自己安排了后事,写好了墓碑题字及楹联。当使者再次来到家里强行催逼时,王徵欲拔刀自刎,经家人多方劝解才作罢。使者无奈,只得让其长子王永春代父从行。临行前,王徵对儿子说:“儿代我死,死孝;我自矢死,死忠。吾父子得以忠孝死,甘如饴也,尚何憾哉!”其慷慨节烈令人叹惜。自此他绝粒不食,七天后离世,终年74岁。 王徵去世后,乡里的贤士大夫感其忠孝之诚、气节之烈,给他取谥号“端节“,称“端节先生“。.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qingtiankuia.com/qtksltx/936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李白醉酒写上联,酒醒后自己却对不出下联,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